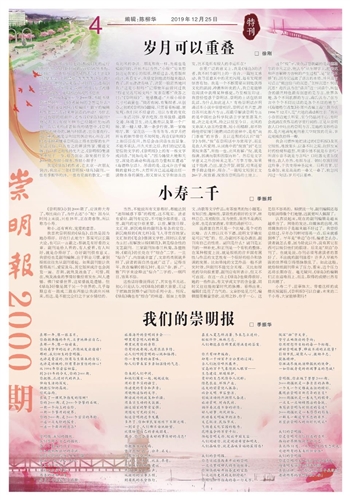光阴似箭,岁月无情,都说时光的运行不可停留,而珍惜时间的古训却流传不朽,比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千字文》“尺璧非宝,寸阴是竞”等等等等,何以故?先是口口相传,后来有了刻划符号,进而创生文字,有了甲骨文、简册、纸张,有了流播文字的载体。文明因之而流传不息也。
《崇明报》诞生至今2000期,不能不使我浮想顿生。创办者最初的念想是什么?第一期的文章因何这样编排?最早的编辑和作者是否有过某种创造的冲动?为什么在这有限的版面中,还专设《绿岛》副刊?物是人非,有很多细节已经随时光而消散。在后来的读者如我的猜想中,《崇明报》是有使命的,她与时俱进,且负重而行,所以重者,她是崇明宣传舆论核心所在,同时还承担着继承崇明岛上得水独厚的生产生活习俗,自古有之的耕读传家、儒道文脉,而日新之而发扬光大之。《崇明报》集诸多重任于一身,艰苦创业、奋发前行至今2000期,斯报小报也,斯报小报乎?
我是《绿岛》的作者,在北京一次朋友到访,我出示三张《崇明报·绿岛》副刊,一张有季振华的诗,一张有兑面的散文,一张有北风的杂谈。朋友和我一样,先前也是编副刊的,开始不以为然,“小报?”后来想到这是我家乡的报纸,便接过去,先看版面设计,再看文字,我感觉到他读得越来越认真了,甚至津津有味了,读罢一脸茫然地问我:“这是小报吗?”记得他年前曾问过我“你老兄还写短文吗?发表在哪?”我答之曰:“《崇明报》”。他感慨道:“大报小报非尺寸可裁量也。”倘若有闲,有集报者,从创办之初的《崇明报》翻阅,只需看看标题,便发现:我们从不经意的、习以为常的变化——生活习俗、穿衣吃饭、住房装修、道路交通、环境卫生、幼儿教育以及第一个广场,第一幢大楼,第一条步行街,第一家咖啡厅,第一家花店……等等等等,当岁月把所有的细节带往不知何处,而在《崇明报》上却历历在目,然后会由词语生出景象。不能不承认,日久天长之后,我们的记忆是要借助文字的,《崇明报》上的有一些文字或词语,“犹如花朵”,“因为她使大地和天空,深处的涌动和高远的力量相互遭遇”(海德格尔语)。吊诡的是,这或许出乎编辑的意料之外,大哲所言已远远超出任一读物本身的属性,却又皆从文字和语言出发,岂不是所有报人的幸运所在?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我是《绿岛》的读者,我不时为副刊上的一首诗、一篇短文感动,我寻觅着其中的灵光闪现,每有发现便惊喜有加。我是一个不断需要从别处获得文化的滋润、冲激和补充的人,我总是能够在阅读中获得某种感觉,乃至相互印证。我曾经惶惑于崇明话、崇明的土话包括田乱话,为什么如此迷人?有些崇明话在明清话本小说中似曾相识,崇明话有古意,源自苏州北部古方言,而最早解读崇明方言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学家张惠英大姐,次之是北风,持之以恒至今日。北风的文章深入语言的堂奥,短小而精辟,却不妨碍他旁征博引驰聘词语的密林中,是有“南门茶座”的芳香。且以近期的《认识“绽”字》为例,“绽”在崇明话中为常用字,而且是农人所爱用,从词典中的“绽放”到“毛豆荚绽来落”,所指一也,北风有解:“绽,就是指满,因满而裂和因裂而补”。然后是文字学意义之外的神来之笔:“万事万物,如果过于饱满、凸出,就会开裂、破裂,结果还要费手脚去缝补、缀合。”一篇短文短到正文260字,绽放着,绽放在崇明岛的土地上。
这个“绽”字,使我浮想联翩的是海德格尔的非凡之论,他认为“从生理学上,把表达和声音解释为音响的产生过程”,是“显然不够”的,因为它远离了语言的本质,并且没有对语言“做出恰当的沉思。”怎样沉思?何谓沉思?海氏认为在“语言”这一词语中,所包含的最具特色最有创意的是方言,世界各地、各个不同族群的方言,海氏认为,“在方言中个个不同说话的是各个不同的地方”(《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12月),是“大地的涌动和生长。”我从小在田边地头听见、至今仍温润于心、有时会流淌在我作品的字里行间的,正是从崇明农人口中吐出的崇明方言,是她的美妙的音韵,是大地涌现地向着天空绽放的花朵,幸运地被我拾得一瓣。
我会习惯性地把读过的《崇明报》及其它报纸,堆放案头,以备不时之需,包括发呆时的检视和遐想,所谓乡情不就是乡音吗?所谓乡音不就是方言吗?口吐莲花者非仅佛也,农人亦然,有报为证。顿时存放旧报这件事,于我变得神圣起来。日积月累,层垒叠加,竟是高高的一叠又一叠了,攸忽间闪过一句话:岁月可以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