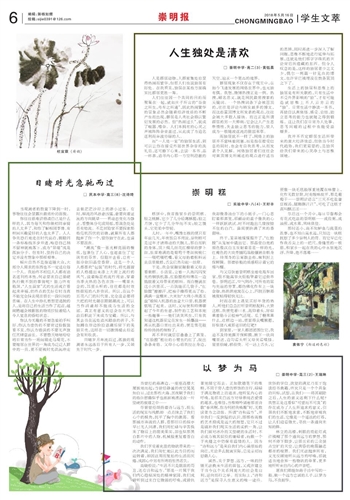糕饼中,我首推家乡的崇明糕。较之桃酥,它少了几分轻薄酥脆;较之月饼,它少了几分华而不实;较之馒头,它更柔中带韧。
儿时,一年中,嘴馋至极的便只有年前几天,年夜饭自不用说,崇明糕可是过年才请得动的大腕儿,那白而软的身体,顶上缀几丝花红柳绿的萝卜丝,肚里堆满的是葡萄干枣丝核桃仁……咂吧咂吧嘴,看父母抬着糕料送去店里做糕,舌尖已然勾起一丝甜。
于是,我会屁颠屁颠黏着父母去看做糕。小店里,立着一人高闪闪发光的钢铁机器,红脸膛的师傅在一边捣鼓着父母带来的糕料。而白糖就在这小店里买,一点钱能买几袋子,“红脸膛”擦擦汗,把袖子撸得更高了些。满满一盆糯米、大米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般倾入机器的血盆大口里,机器便低吼了起来。这时,父母便和师傅聊起了今年的生意,制作的工艺和本地一些趣事……他们谈笑风生,只有我知道这机器里定在发生一场鏖战——再从机器口里吐出来的,便是雪花般纷纷扬扬的细粉了。
再不多时就层层叠叠上了蒸笼。“红脸膛”粗壮的小臂也灼红了,绽出条条青筋。父母小心将我拉在身边,我却像香油台下的小耗子,一门心思盯着那蒸笼,那颤动的盖子像我的心一样跃跃欲试,时不时跑出几缕按捺不住的白汽。鼻间便挤满了米的香甜味。
终于,笼盖被缓缓揭开了,“红脸膛”从笼屉中撬出它。那晶莹白亮的颜色像汉白玉反射着星星一样的光,红褐色的大块枣脯玛瑙般镶嵌在糕身上。待周身的云雾散去些,麻利封上保鲜膜。那磨砂般的质感昭示着它的绵与糯。
与父母驮着崇明糕坐着电瓶车回家,恨不能高举火炬般擎着它过街串巷。崇明近江,空气阴冷,可所有的寒与先前的劳累,都仿佛化作车上一块食物,热烘烘地窝在心上,四肢百骸都被熨帖得轻快无比。
时而在街上遇见买好年货的熟人,听他们急急打听崇明糕配料,大赞这糕,我便兜着口水、高仰着头,好似乘着筋斗云般神气活现。瓜子糖果算什么,往糕边一站,便显得尖嘴猴腮,好似猪八戒那老旧的钉耙!
到家里,一家人都团团围住它,我迫不及待地撕开保鲜膜,揪下一块向嘴里送,边勾着头听父母笑着嗔怪。屋里很暖,糕很烫。可一沾上舌头,它便像一块毛毯般厚重地覆在味蕾上,化作无数甘甜,时有酸味绽开,那是葡萄干……崇明谚语言“三天不吃盐齑豆板汤,腿脚酥汪汪”,可吃了这糕才真叫酥汪汪……
尔后这一个月中,每日早餐都会有花式吃法的崇明糕——或佐粥,或油煎,或水蒸,风味俱佳。
那时还小,尚不知鲈鱼与莼菜的故事,也不知山高水远,只知这一块糕抚慰了多少崇明人的胃。而它早已化作我舌尖上的一把尺,骨缝里的一根筋,和家乡一起在我的心中永恒地沉浮,升降,绝不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