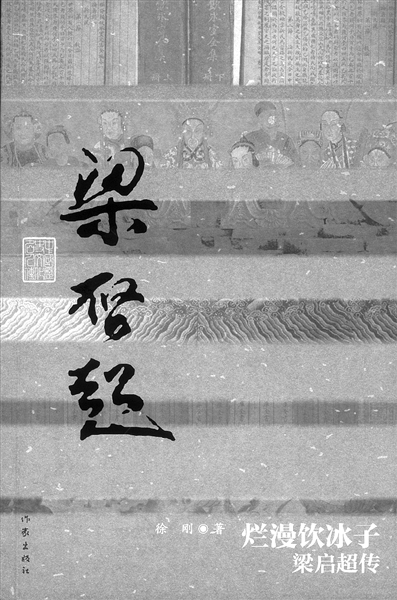寻觅于饮冰室,在长彗琼花间漫步,我仿佛看见,走出这情感飞动的时空隧道,一个死去的伟人和他蒙尘的思想正在复活。
这些年来写梁启超的、关注梁启超以及他所处的民国时代的人多了,这实在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幸事,此种现象或可多多少少地减轻我们数典忘祖的罪过,或者还能引发文化复兴的渺远之想。然而要让追思追问先哲的现象,成为一种思潮,成为“连续不断的群众运动”(梁启超语)还需时日,还需更多的前仆后继者,还需要我们远离尘嚣地从历史人物身上,从他的洋洋大著中以若干新见解、新观点奉献给社会及读者。以梁启超治学之论,史学是“将过去的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借鉴”,且要有“新目的”。那么梁启超一生“新意义”、“新价值”何在?是否能震烁于二○一三年的中国社会,从而使我们这些“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得到借鉴乃至灌顶而猛然醒悟呢?
或者也可这样说,我们不能再泛泛地写梁启超了,这个时代需要的是以史学的眼光解读梁启超,并且要“别具只眼”(梁启超语)。这一点,我自己就是不合格的。虽然,从一九九六年首版《梁启超传》始,二○○六年重修,二○一○年再修,内心所得的观感,对梁任公依然是望若河汉,而自己一改再改的作品不过是浮光掠影,是次又修订删改,欲以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攻”梁启超,在他的原著及史料中以他所教的“钩沉法”去钩沉他,便钩出了散见于千百万文字中,安详平静地蛰伏着的梁启超的音容思想,得着犹如为今而发的感慨!书成,我把这些所获所感,举其要者,着重于社会心理、文化教育,以为引子。
梁启超够得上思想家的称号吗?梁启超的思想是“肤浅”(陈独秀语),还是深刻?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流亡日本时与《民报》笔战,在历史上其绵延之影响不绝于今世者,为《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一文,任公明言:“私有制度,虽谓为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可也。”为什么这样说?任公有详解:“就历史上观察人类之普通性质,以研究现经济社会进化之动机”;“人类有欲望之故,而种种之经济行为生焉,而所谓经济上之欲望,则财务归于自己支配之欲望是也”;“惟归于自己支配,得自由消费之、使用之、转移之,然后对于种种经济行为,得以安故”;“故今日一切经济行为,殆无不以所有权为基础,而活动于其上”。任公又谓:“盖经济之最大动机,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梁启超同时还指出,土地国有化的根本危机,是将国家立根之本、农民衣食之源的土地,“悉委诸官吏之手,则官吏之权力必更畸重,人民无施监督之途,而所谓民主专制之恶现象,终不可得避”。此种“恶现象”为何?官吏控制之下的土地财政,并且以国家的名义支配,“所谓国家以大资本家而经营者,亦限于独占事业而已……其结果势必尽吸一国之游资于中央,而无复余裕供给私人企业之需要,则一国中无复大资本家出现,诚哉然焉,但不识当时国民经济之状况,其萎敝若何耳!”何止经济,“然则此制度足以令政治趋于腐败,又必至之符矣”。
读者至此会生出何种感想,我不去揣测,以上文字,可谓梁启超有大思想家之目光如炬乎?倘仍感不足,不妨再列举任公于二十世纪之初访新大陆游记一端。其时适逢美国罗斯福总统巡视太平洋沿岸,并有讲演称“太平洋,洋中之最大者也,而此最大洋,在今世纪中,当为吾美国独一无二之势力范围”等语。梁启超据此有太平洋与中国之论:“世界大势日集中于太平洋,此稍知时局者所能道也;世界大势何以日集中于太平洋?曰:以世界大势日集中于中国故,此又稍知时局者所能道也;若是乎其地位可以利用太平洋以左右世界者,宜莫如中国。中国不能自为太平洋之主人翁,而拱手以让他人,吾又安忍言太平洋哉!”任公不忍言,我辈无以言,虽不忍言,虽无以言,今世今日太平洋上风涛能拒之不闻吗?
梁启超以最后十年的心力教书讲演,或可再问,在梁启超所处的日益西化的时代背景下任公坚守者为何?反对者为何?
梁启超对“教育”的一贯主张为“教人学做人”,后来在这一句话之后又加了一句话“学做现代人”。在《北海谈话录》中自谓做清华国学院导师,“当然有我的相当抱负而来: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它体现出来”。那么,《先秦政治思想》、《儒家哲学》、《戴东原哲学》及孔、老、墨、荀研究等等,都可做“底子”看,这个“底子”里不仅有学问,还有做人的道理及“人格上磨炼”的方法,任公嘱同学诸子,“自己先把做人的基础打定了”,且要有“道德信仰”,然后是“做人做学问”。当时的教育现状又如何?梁启超说“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了”。“现在的学校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上课下课,闹得头昏眼花。进学校的人大多数除了以得毕业文凭为目的外,更没有所谓意志,”是次北海谈话在一九二七年初夏。而在一九二三年南京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中任公便说过:“现在中国的学校,简直可说是贩卖知识的杂货店,文哲工商,各有经理,一般来求学的,也完全以顾客自命。”这种只讲知识,不求精神和人格培养的教育,“我以为长此以往,一定会发生不好的现象。中国现今政治上的腐败,何尝不是前二十年教育不良的结果?”教育不良会生出政治上的腐败,任公所教也。教育不良所生的另一恶果便是“精神饥荒”,对于此种饥荒更可怕的是“人多不自知”,仍以为只是“知识饥荒”。
梁启超认为,救济“精神饥荒”之要者,首要就是立精神生活为第一。“物质生活,仅视为补助精神生活的一种工具”,“最要,在求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精神生活贵能对物质界宣告独立;至少,要不受其牵制”。而东方精神,“即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
梁启超还认为,“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一点为好。……知识愈多,痛苦愈甚,作歹事的本领也增多”,“大奸慝的卖国贼,都是知识阶级的人做的”。一九二二年,在苏州学生联合会讲演,任公先讲:“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词地答道:‘为的是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替你总答一句罢:‘为的是学做人。’”在道德的意义上,怎样成一个人?任公的教导是:“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智、仁、勇。”为什么叫做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通的道德标准,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即任公说的“完成状态”又是什么样的呢?那就是孔子所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此即伟男子、大丈夫”,也就是“成一个人”了。
梁启超认为“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现在讲的智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梁启超对这三个方面的概括为:所谓“智者不惑”的必要条件,是具有“常识和学识的总体智慧,方能不惑”;所谓“仁者不忧”,“仁”字是说人格之完成,所以孔子说“仁者人也”,“仁”字从二人,因何?梁启超释义为:“总而言之,要彼我交感互发,成为一体,然后我的人格才能实现。所以我们若不讲人格主义,那便无话可说。讲到这个主义,当然归宿到普遍人格。换句话说:宇宙即人生,人生即宇宙,我的人格和宇宙无二无别。”然而何以因此无忧?因为我们知道了“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易经》六十四卦,始于《乾》而终于《未济》,正因永不圆满才有永远的创造和新生。“‘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凡做事便不会失败。”“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不仅不忧而且自得怡然,“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梁启超的写照。“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是教人做到仁者不忧。”既不惑且不忧,又养“浩然之气”,“‘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才算顶天立地做一世人,绝不会有藏头躲尾左支右绌的丑态。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教人做到‘勇者不惧’。”
梁启超是次讲演之末,几乎是大声疾呼了:“诸君啊,你千万不要以为得些片断的知识就算是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你罢:你如果做成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你不信吗?试想想全国人民所唾骂的卖国贼某人某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试想全国人民痛恨的官僚政客——专门助军阀作恶鱼肉良民的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这些人当几十年前在学校的时代,意气横历,天真烂漫,何尝不和诸君一样?为什么就会堕落到这步田地呀?”梁启超情不可抑,吟诵了屈原的几句诗:
何昔日之芳草兮,
今直为此萧艾也!
岂其有他故兮,
莫好修之害也。
梁启超是现代科学、科学思想的热诚拥护者、传播者,又是科学万能、科学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五四运动之后,舶来了“德先生”、“赛先生”。当时国中不少人认为,有了科学就什么都好了,是有科学与玄学的丁、张论战。梁启超认为“不能用科学来统一人生观”,在《人生观与科学》一文中说,人类生活固然离不开理智,但倘以理智涵括全部人类生活那就错了。所不能包括者为何?任公说:“还有极重要的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现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梁启超并且以“爱先生”、“美先生”称之,又谓:“‘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
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正是“情育”、“意育”的化身。有之,得大义凛然;无之,生暴戾凶残;有之,为清廉诚信;无之,则腐败卖国。任公发明的“爱先生”、“美先生”,衡量时下,其“新意义”不若惊雷闪电乎?
泰戈尔说过,“我们不能借贷历史”,中国人则厚今忘古,善忘、健忘历史。梁启超很早便指出了中国国民性中“健忘”的特症,一是在反袁战争结束后《五年之教训》的结句:“呜呼!毋忘!毋忘!呜呼!吾其如此健忘之民呵!”另一处稍晚载一九一五年七月《大中华》的《复古思潮平议》中,“甚矣!国人之善忘也”。梁启超开创《新史学》,带有“史性”的写作贯于毕生,尤其是学术成就最辉煌的最后十年,不仅几乎日日讲史,而且反复地讲历史研究法。任公何忧?忧当时人、后来人以历史为敝屣,忘犹过之也。所以梁启超一再呼告,像传道人之荒漠呼告一样:“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药。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史学到底具有何种意义?何种魔力?任公称:“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切实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
梁启超在史学研究和写作中,因为得着“明镜”,使他成了最无情的自我解剖、自我讨伐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论自己:“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者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又:“启超务广而荒,……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裂山泽以辟新局,就此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之陈涉。”梁启超自比陈胜,让他当时的一班做文章的朋友很是吃惊。任公有自谦,但也极自信且坦坦荡荡地说:“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之规模。”国人期望之重,任公又自许、自励、自叹:“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上不能不谓一大之损失也。”
梁启超的这一番话,其实正是在思想界造出一大境界的开始,《清代学术概论》写作前后,梁启超以《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儒家哲学》、《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气象宏阔、缜密精湛的鸿篇大著,架构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开国规模”,称之为先驱者、缔造者,不为过也。
……
要感觉梁启超笔端浓得化也化不开的爱,还要读《梁启超年谱长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中,他写给“放洋”的儿女们的信,他把最富爱的魅力的言词,都给孩子们了,“大宝贝”,“小宝贝”,“对岸的一群大大小小的宝贝们”,家事国事著述等等,还有家庭生活中的趣事,皆与孩子们分享。但自己血尿之初,后来几小时、几十小时的小便堵塞的痛楚,却从未主动言及,只是告诉大女儿思顺:“我平常想你还可以,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他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梁启超把对孩子们的情感,以爱情名之,儿女情长之极者也。任公对孩子们完全是爱的情感教育,然后是人格修养,习惯的提醒。梁启超,伟大的父亲!
我雅不愿以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史学家,伟大的教育家,伟大的文学家,祝告于西山任公墓前,可是我又怕任公责为“哕嗦”,为史极不可有一点夸张之嫌。虽然,我欲辩之,末学岂敢?故以任公为文简洁之好,剪而裁之曰:一代宗师。
可乎?可乎?
摘自《烂漫饮冰子:梁启超传》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