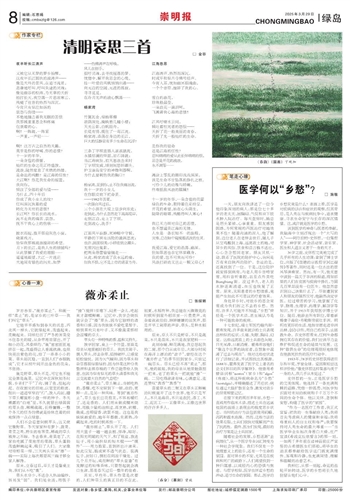□ 张绥娟
岁亦春至,“薇亦柔止”。和薇一样“柔止”的,是家乡的三叶草——我们叫它“草头”。
它能早早感知到春天的讯息,西北风一掉头,它就绿起来,茂盛起来,柔嫩起来。同样经历了严冬的荠菜受不住春光的暖,从杂草堆里冒出,开了细小的花,风姿绰约。“薇”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茂盛得让人垂涎欲滴,也很快亮出紫色的花,结了一串串小小的荚。草头却沉稳,一直到人们“春服既成”,它才从枝叶间开出金色的花朵,不张扬。
薇是野草,草头不是,可它也不能完全算是蔬菜。记忆中在深秋初冬时候,乡亲们“干”了沟,捕了鱼,挖起沟泥。在收割完的田地,以宽宽的距离,削出一道道窄窄的“行”,放入沟泥,播下草头螺旋形小盘一样的种子。冬天裸露的“白地”里,不久就冒出绿茵茵的草头苗,稀稀疏疏,长得慵懒,一整个冬天的任务仿佛就是给休息着的田地保持一点点绿意。
人们不会着意伺候草头,这又使它像野草。冬天家家种有萝卜、菠菜、青菜之类,野生的有荠菜,稀疏的草头被弃之不顾。冬去春来,青菜老了,大家也吃腻了菜地里的菜蔬,草头蓬勃茂盛鲜嫩起来,吸引了人们。大家像对待野菜一样,三天两头采来“搂”一碗——实际上每次都要两三碗才够全家人解馋。
原来,立春过后,草头才是餐桌主角,我们从不吃“薇”。
草头水分少,不适合入热油煸炒,容易发“韧”。我们是汆汤,用筷子“搂”(搅拌)至瘪下,闷煮一会儿,吃起来才甜糯鲜嫩。记忆中,我学会烧饭就学会了“搂”草头,因为它独特的清香和口感,因为我妹妹不爱吃菜帮子,特别喜欢只有叶子、又不像菠菜那样会涩嘴的草头。
草头有一种特殊的香,温和又持久。
放学回家,桌上一个竹篮,里面是母亲从地里割好的草头。我找来筛子,倒入草头,择去杂草,掐掉硬杆,总感觉轻松愉悦。因为天气暖和,因为草头和杂草都碧绿碧绿的,因为择菜这种分类整理和去粗存精的工作总能带给人快意,也因为似有似无的草头清香和我无言交流着大自然的气息吧?
“薇亦柔止”,草头嫩止,当顿吃热的,香糯,吃不完留到下一顿,凉的,更鲜一点,是另一种风味。等到“薇亦作止”,草头也长出花苞来,不容易嚼烂了,还是香的。人们用来做成糯米烧饼,用极少量的油煎过,再烹熟,软糯、微咸,齿颊留香,欲罢不能。这也是我妹妹最爱的,她年年都做,先蒸熟,冷藏起来,吃的时候再煎一下。
“薇亦刚止”,草头开了花。人们用大篮子一趟一趟去割,择净,晾好。在阳光明媚的天气下,和了粗盐,放进坛子,用小扁担似的短木棍——“揲杵”——用力捣紧,直到挤出汁液来。如此反复,捣成密不透气状态。装满坛子,封好口,倒扣在阴凉干燥处。过几个月开坛,咸而鲜的“草头盐齑”有发酵过的特殊香味,只要想起就会满口生津,那是春天过后一整年的佳肴。
其实,早些年,草头作菜是次要的,人们种草头的真正目的不在此。初夏,水稻育种,我总能在天微微亮的时候听到屋外稻田里一片橐橐声,夹杂着叔叔伯伯、婶婶嬷嬷的说笑声,那是开早工剁草的声音,草头,是种水稻用的。
原来,草头不只是野草,不只是蔬菜,不只是苗床,不只是农家肥料……
此刻春暖,鲜花满地,我总想起我的二舅,那个自从成年后,大部分时间在海洋上漂泊的“游子”,曾经在这个“薇亦作止”的季节回到家乡,只惦记一碗草头。草头已经不再“柔止”,那天,他的姐姐,我的母亲从地里勉强割一把来,老了的草头一把就能“搂”一碗。二舅吃得津津有味,心满意足,连连赞叹“真香”“真香”!
喜爱草头的二舅又在草头正鲜嫩的时候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不只是军人,不只是海员,不只是农民、漆工、木工、泥瓦工……正像草头,正像这世界的许许多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