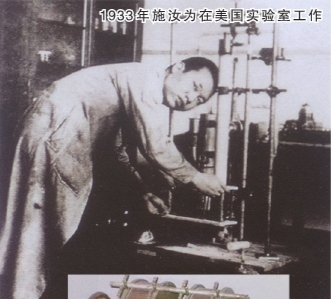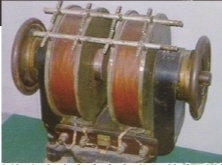施汝为(1901-1983),崇明县港西镇人。物理学家,我国现代磁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1954-1983年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创始人,美国耶鲁大学物理学博士。在铁磁合金和磁铁矿的磁晶各向异性、磁畴观察研究和铝镍钴系永磁合金磁性改进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磁学研究实验室,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磁学专门人才。
学成回国创建中国第—个磁学研究实验室
1901年11月19日,当启明星升起的时候,施汝为(号舜若)出生在崇明上沙协兴镇(今港西镇北闸村3队)一个耕读之家。祖父读过唐诗宋词,也懂一点星象占卜,视长孙为“星宿”,对着襁褓中的孙儿喃喃地说:“汝当可为”。
1917年,施汝为考入江苏省立第一工业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因社会动荡和家庭经济原因,转入江苏省海门中学。海门和崇明半江之隔,那里是中国末代状元张謇的故乡,不远处,还有更有名的范仲淹,也是当代著名数学家杨乐的故乡。染海门名士之风,汲海门地气之灵,施汝为青年时代就有志气和毅力,深深感悟范文正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920年,施汝为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科学习机械。1923年,工科并入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施汝为经过反复思考,转攻物理学,师从中国物理学界一代宗师叶企孙。1925年,叶企孙应聘北上清华大学任教,刚毕业的施汝为随恩师北上任助教,并在恩师指导下专攻磁学。施汝为通过相关研究,已经预见到电磁学的广阔应用前景。
1930年,施汝为因为业绩突出,被选送美国伊利诺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华罗庚、竺可桢也在那里工作或学习过。一年后,施汝为获硕士学位并转学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世界著名磁学家麦基恩教授,1934年,施汝为获博士学位。此时,日寇正在蚕食中国。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召施汝为回国报效祖国,同年8月回国,任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丁西林,严济慈、胡刚复、杨肇镰等也是该所研究员,地址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路)。施汝为一边着手建设中国第一个磁学研究实验室,一边继续他的博士论文续作。不久,淞沪会战爆发,施汝为和他的团队不得不中断研究。1938年,研究所迁往广西桂林,施汝为兼任广西大学机械系教授,工作更加繁重,但他乐此不疲,科研、教学双获成果,丁西林视之为干城股肱。
珠联璧合为中国物理事业比翼双飞
在桂林,施汝为与顾静徽相识,结为伉丽。顾静徽,江苏太仓人,1900年出生,中国第一个留美物理学博士,在国内读书时曾师从胡刚复,学成回国后任南开大学物理系主任,那是继中国物理学宗师饶毓泰之后南开大学物理系第二任主任,核物理女王吴健雄在国内时曾师从顾静徽。顾静徽为人可爱,高贵而宁静,从不矫揉造作,且乐于助人极有同情心,不但细腻,而且宽容大度敢于担当,连好些自以为江湖侠义的男人也自叹不如。施汝为虽出身农家,但儒雅谦恭、好学有才,两人珠联璧合,“比翼双飞”。据说,所长丁西林是顾、施两人的作媒之人。
1945年,抗战胜利。施汝为奉命接收日寇在上海建立的“自然科学研究所”。当时,老百姓讽刺国民党官员的接收为“劫收”、“劫搜”。施汝为一尘不染,将所有接收的财物一一归公,保持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
1946年,昆明发生“李闻血案”,1947年,南京发生“五二〇”惨案。施汝为对国民政府越来越失望。1949年,国民党“抢运学人”去台湾,施汝为严辞拒绝,和物理所大多数同事一起迎接新中国。
1955年,施汝为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但他一直拒绝领取占工资比例很大的学部委员(院士)津贴。而在“文革”中,物理所处于瘫痪状态,施汝为无法正常工作,觉得愧拿工资,将每月工资一半交党费。施汝为治学严谨,在物理王国中,他是一个绅士,潇洒、挺拔、高大,有大将风度。但在生活上,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的生活很节俭。1956年,施汝为夫妇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殚精竭虑打造国际物理学界有重要
影响的研究所
1956年夏,施汝为和周培源等科学家一起参与制订12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并被正式任命为物理所所长,开始他长达25年的“所长任期”。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施汝为随同中国科学院代表团一起抵达莫斯科,参加中苏科学界的谈判。
1958年,施汝为兼任新创办的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主任。在新生座谈会上,施汝为讲了“李约瑟之谜”,激起学生的民族尊严。施汝为亲自为本科生授课,他启发学生说:“知识哲学有三个层次——求学、求真、求智慧。求学是为了求真,是负责任。有了高度负责的精神,才可能有激情、有动力。只有有了激情,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施汝为还勉励学生要有挑战权威的志气和勇气。施汝为对夫人说,作为中国最高科技级别的大学物理系主任,他有责任正确地引导学子。他对女儿说,做学问如同做人,做人也是做学问,先做人,然后才能做好学问。施汝为借用马克思的话对当大学教师的女儿说:“诗人为了写诗而写诗,诗人就不成其为诗人。同样,教师若为稻粱谋而教书,也不成其为教师。”某节日,施汝为送给大女儿俄文版《爱因斯坦传》,这是他出访苏联买的唯一私人物品。施汝为对大女儿说,爱因斯坦的品德是真正的科学精神:一种不带成见、少偏见、少贪欲、少功利的平常心、干净心、活泼心、好奇心、进取心。科学也慰藉了爱因斯坦的心灵,在他看来,研究本身就是幸福,而得到的巨大成就,则是附带结果。“文革”过后,施汝为在桂林出生的小儿子被委任为某科研部门负责人,上任前,施汝为用他漂亮的苏体字写了个条幅送行:为而不恃,无欲则刚。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任重道远,诚而善思。
1960年3月,虽然时令依然春意盎然,但世事正是黑云压城。就在中苏“密月”即将结束的时候,施汝为率领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并在苏联科学院物理所作学术报告。他的俄文已经自学到相当高的水平,连同他在学术上的真知灼见,得到苏联同行的热烈赞扬。同年5月,施汝为在北京会见巴西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就量子力学和几何学等方面进行交流。施汝为对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充满信心,正像他在第二届全国物理学会年会工作报告中所说的:“我国物理学已具备一定的基础和一定的有利条件,只要我们永远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前途是光明远大的。”
1972年,杨振宁、李政道以及巴丁等访问中科院物理所,施汝为开始参加外事活动。1973年,施汝为陪同郭沫若、吴有训、周培源会见加拿大科学家代表团。三周后,施汝为携夫人顾静徽,陪同周恩来总理会见并宴请吴健雄、袁家骝夫妇。1977年10月27日,国务院任命施汝为继续担任中科院物理所所长。1978年,中国物理学会在庐山召开年会,“少长咸集,群贤毕至”,钱三强代表上届理事会作工作报告,施汝为致闭幕词。会议期间,施汝为和无话不谈的相知周培源谈教育问题。施汝为说,大学是一个民族的科学共同体,一个民族的精神中心,是追求真理的地方。如果人生在知识领域中的一切活动都只是为了追求实际的利益,那么世界上就不会有学问和真理。所以,一定要重视大学的生存发展方式。
1981年,施汝为辞去所长职务,任物理所名誉所长。
呕心沥血为中国磁学开创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上世纪30年代初,施汝为采用原子(分子)磁团间距受水的影响而改变的模型,解释了所测得的实验结果。在研究含铁低于5%的金——铁合金时,观测到这种合金的顺磁性,但却不符合顺磁性的居里定律或居里—外斯定律,而是磁化率平方根与铁含量成正比;当铁含量为10%时,合金从顺磁性变为铁磁性。
在上世纪30年代,施汝为同他的导师改进了传统用于抗磁性和顺磁性测量的五线摆磁强计,增强其均匀磁场强度,在样品移动方向再加——低梯度磁场,又采用读数显微镜测量摆的偏移,显著地提高了仪器的灵敏度,因而可用于毫米级小铁磁样品的精密测量。
更为重要的是:他一是对铁磁(性)合金单晶体的磁晶各向异性的开创性研究。上世纪30年代,施汝为关于铁——钴系和镍——钴系铁磁合金单晶体的各主轴磁化曲线和磁晶各向异性的研究是其重要的发展。施汝为在这些研究中首次提出,铁磁晶体的易磁化方向不仅依赖于晶体结构,而且与晶体所包含的原子种类有关。他在这些铁磁合金中首次发现其易磁化方向随合金成分的改变而变化;二是对铁磁合金和磁铁矿单晶体及铁磁多晶体的磁畴观测研究。1907年提出磁畴假设(铁磁性理论两大基础之一)后,前人在1932年才用磁粉纹图方法直接观测到磁畴结构。施汝为对多种典型的铁磁材料的磁畴进行了较仔细的观测研究,其中一部分研究成果是在抗日战争十分困难的环境中完成和发表的;三是对铝镍钴系永磁合金的改善磁性和探讨磁硬化机理的研究。对铝镍钴系永磁合金的改善磁性和探讨磁硬化机理的研究,是一项密切结合国家经济建设需要的研究工作。施汝为同他的合作者采用改进热处理工艺的方法使国内工厂生产的铝镍钻永磁合金的最大磁能积提高约1.5倍。他们还发现铝镍钴5永磁合金经适当的磁场热处理后的矫顽力增加远大于磁各向异性的增加,磁转矩在600℃—680℃间从可逆变化转变为不可逆变化。这些研究都为改善这类永磁合金性能和探讨其磁硬化机理提供了有意义的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积极拥护国家的各项政策,对蓬勃开展的经济建设满怀热情,尽力为其服务。在他领导下应用物理研究所开展了当时工业上急需的永磁合金和硅钢片性能改进的研究工作,他亲自领导和参加的关于铝镍钻永磁合金的研究工作和磁硬化机理的基础性工作。1953年,他看到发展非金属磁性和材料研究对于无线电电子学技术的重要性,因而组建磁学研究组。
1983年月1月18日,施汝为在北京逝世。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三强致悼词。悼词中说:施汝为同志“是我国现代磁学研究的先驱者、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是一位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老科学家”,“他为国为民,唯独不为自己”,“他十分重视培养人才,为出成果、出人才,兢兢业业,呕心沥血,把毕生的精力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带头人,任人唯贤,克已奉公,生活简朴,反对特殊化,以身作则,秉性正直,对拉拉扯扯的庸俗作风深恶痛绝”。
本文作者为上海市崇明文史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