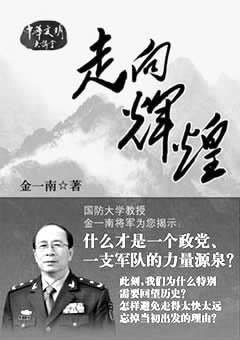中国红色政权为何能存在
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开始的时候,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许多人并不看好中国共产党,他们看好的可能还是中国国民党。中国革命充满了很多问号。
中国革命中令人费解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也被称为中国革命的“斯芬克斯之谜”。
斯大林不看好中国共产党,那么他看好谁呢?斯大林起先看好的是军阀吴佩孚。北洋政府时期,吴佩孚曾掌握着权力,他也做出革命的姿态,提出了要铲除帝国主义等许多主张。
后来,斯大林看好的是中国国民党。要知道,当时中国国民党是第三国际的友党。第三国际召开大会,中国国民党也派代表参加,蒋介石就作为代表去过苏联。
第三国际的大会上,代表们慷慨激昂地号召进行世界革命。在那种情况下,斯大林有一个判断,他认为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雅各宾党人。他拿法国大革命来类比,具体来说,蒋介石是中国大革命的罗伯斯比尔。最后他发现对蒋介石做了错误的判断。
18岁时,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
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1911年他考入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有生以来看到的第一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上面刊载广州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毛泽东说:“我是如此地激动,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院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孙中山长毛泽东27岁,但他也知道毛泽东。那时,他要把国民党改头换面,将其整个组织体制全部改变,按照苏俄的建党模式重新建立国民党。在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一大”上,有两个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共产党员,以能言善辩、词锋激烈给国民党元老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是李立三,一个是毛泽东。
李立三单刀直入,大段大段阐发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率直批判国民党的言论;毛泽东主要以孙中山的说法为依据,论证自己的观点。
许多国民党人惊异地注视着这两个人。孙中山以赞许的眼光,注视着这两个新锐。他亲自批准毛泽东为章程审查委员。
但孙中山对共产党青年新锐的欣赏,并不等于他就同意共产党的主张和共产党的革命道路。孙中山不相信红色政权能够在中国存在。
1928年10月,秋收起义上井冈山一年有余,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分量非常重,最根本地揭示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中国发生的革命,为什么有这可能?为什么能够做下去?为什么能够成功?这篇文章解答了中国革命的“斯芬克斯之谜”。
毛泽东回答问题是:实事求是。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专门谈“中国红色政权发展和存在的原因”五条原因中的第一条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即军阀混战。
毛泽东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什么条件呢?第一条就是:“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条。所以才有了鄂豫皖、湘鄂赣、湘赣、闽浙赣、川滇黔等边区。
也正是由于这样,才有了突破四道封锁线时,红军与陈济棠的协议。这还表现在湘江之战白崇禧的半心半意,以及蒋与贵州军阀王家烈和四川军阀刘湘之间的矛盾。这样的因素贯穿长征道路的大部分。
文章继续写道,第二条是受革命运动影响的地区,第三条是全国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第四条是相当力量的正规红军存在,第五条是党组织的有力量和政策不错误。
毛泽东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实指的是这五条(红色武装放在了第四条)。说到枪杆子,蒋介石的枪杆子不比毛泽东多?玩得不比毛泽东熟?为什么蒋介石却是“枪杆子里面丢政权”?不得不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认识非常深刻,解开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的谜团。
当年认定“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的孙中山,如果知道最终由他的后进——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建成了“强盛独立之中国”,难道不也会同样感到欣慰吗?
惊天动地的革命年代过去了,这个问题并没有简单地过去。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法国《世界报》5月29日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新的社会契约》,可以说是间接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文章说:“每一次中国出现危机,都会有共产党垮台的预言。垮台论的预言家没有看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反思让其表现出全球共产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可塑性。他们所具有的快速调整、自我批评以及不断考察国外有效模式等灵活方式,不但巩固了其政治基础,而且还具有与民众达成一种新的社会契约的能力。这种契约基于经济效率和爱国主义(或曰民族主义)两根支柱。”
所谓“可塑性”,从另一角度来说,就是历史自觉。
也许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评价。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新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表现出的可塑性,是一个政权生命力和发展力的来源。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努力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就不断获得发展,不断获得进步。
长征:命运的抉择
长征是中国革命中最伟大的史诗。
历史将会证明,它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石。
长征中蕴涵着精神财富。
世界各国对长征的评价显示,中国共产党人像一只不死鸟,就是我们所讲的涅槃的凤凰。经过这样的经历,这支队伍,这个政党,它所领导的事业难以被摧毁。
任何史诗中的那种雄浑壮阔、那种波澜起伏、那种令人心驰神往的伟大辉煌,都是对后人而言的。
史诗也好,奠基石也好,都是后人在历史长河中的评价。
长征是不是一次仓皇的撤退、无目标的突围?
当时是走,还是留?走,往哪个方向走?对当事人而言,则是不尽的流血牺牲、不尽的挫折苦难、不尽的矛盾斗争。
实际上,从历史过程上看,并不是到了1934年10月长征前夕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如此严峻,然后,中央领导才做出这样的决策。
在此以前,项英曾经最早提出过放弃中央苏区的意见。
1931年4月第二次反“围剿”,项英到苏区时间不长,认为20万敌军压境,3万红军难于应付,只有离开江西苏区才是出路。退到哪里去呢?
项英提出退到四川去。因为斯大林讲过:“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根据地。”
第二个提出离开中央苏区作战的,是彭德怀。
第五次反“围剿”遭受挫折,彭德怀率先提出脱离苏区,外线作战。
不光是我们在总结经验,对方也在总结经验。
第五次“围剿”,蒋介石、陈诚把红军作战方法和过去他们所吃的亏进行了总结。第五次“围剿”实行堡垒战术,步步深入,步步推进,极力避免孤军深入。敌人的长进,再加上红军错误的战术指导,甚至战略指导——短促突击,苏区反“围剿”面临很大的困难。
第五次反“围剿”刚打了一个多月,彭德怀也看出情况不妙。
1933年10月23日至25日彭德怀、滕代远连续三次向军委建议,改变战略方针与作战部署,主力离开敌人堡垒区向外线出击,机动作战,迫敌回援。
彭、滕提出外线作战,是跳出封锁线向苏区东北的金溪、东乡、贵溪、景德镇挺进。不展开地图标出苏区界限和进击的地点方向,你就不会知道这个建议有多么的大胆。
第二次反“围剿”时,项英提出去四川的建议;第五次反“围剿”前期,彭德怀提出以主力跳出中央苏区的建议,都被否决了。
当然,项英当时的建议是错误的;而彭德怀是在一线作战的指挥员,已经觉得当时态势的危险,必须采取另外的战略战术,但是也被否决了。
1934年4月底广昌战斗彻底失利之后,中央书记处于5月开会,决定突围转移。当时的书记处书记是四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这是按在党内的地位排的顺序,博古负总责,张闻天负责宣传,周恩来负责组织,项英是中革军委主席。代表“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的毛泽东不是书记,无法参加会议。决策在博、张、周、项四人中做出。对这个事关重大的会议的记录一直很少,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决定了中央红军进行突围。
对中共中央书记处战略转移的决定,6月25日共产国际回电:“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促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
博古对李德说,国际来电同意。
其实,国际的表态含糊不清。首要的是“保存活的力量”自然正确,但“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促使我们惊慌失措”,又认为打破“围剿”的希望还不是没有;具体怎么办,实际上是留给中共中央自己决定。如果你们觉得能够守住的话,你们就继续守;如果觉得主力不能再这样消耗下去,你们就走。实际上又把皮球踢了回来。其中的关键原因,不是共产国际不想决策,不是说它要推卸责任,而是对中共革命的详情不甚清楚。
1934年7月上旬,各路敌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发起全面进攻。
8月5日,北路敌军9个师,在飞机、炮兵的强大火力支援下,向我三军团主力在高虎脑、万年亭一带构筑的5道防御阵地展开猛烈进攻。
在敌人炮火猛烈轰击之下,红军阵地工事全部被炸塌,机枪被炸坏。血战至下午,蜡烛形阵地的三营损失严重,张震带着全营仍然能够战斗的人坚守在一条交通壕内,准备用刺刀同敌人作最后一拼。保护山阵地尽管放上了全军闻名的红五连,但在敌人优势兵力、火力压迫下,阵地失守,红五连大部壮烈牺牲。
红军十日内伤亡2300余人,内含干部600人。
尽管9月1日至3日,朱德指挥林彪的红一军团、罗炳辉的红九军团取得温坊大捷,歼敌一个多旅,取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次难得胜利,但被动局面已无法改变。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在于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狭小的区域之内。
战略转移已成定局。
5月初,李德受托起草5-7月季度作战计划。计划的核心已经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深入敌后。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不是李德自己想制定计划,而是中共中央把权利给了他,具体说,包括博古等人把权利给了他。
7月底,李德再次受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之托,制定8-10月作战计划,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问题已正式提出。
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全面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