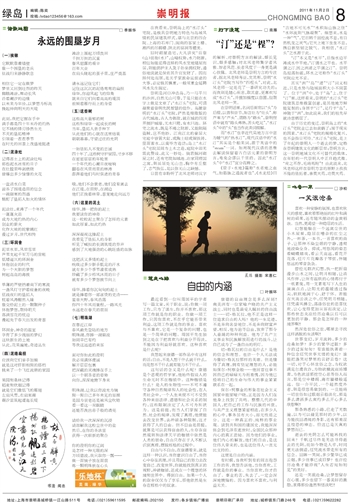□南雁
在我看来,崇明岛上的“水汀头”宅院,是极具崇明地方特色与岛域风情的民居建筑样式,堪与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闽南的客家土楼、湘西的吊脚楼、陕北的窑洞等媲美。
旧时砌屋造宅,大凡讲究“后靠(山)前抱(水)”,山喻权势,水乃财源,相信如能觅得这样的风水宝地建屋而居,则能荫护主人及子孙坐拥权财,通俗地说就是保佑其升官发财了。因而择何处而居,是关乎家族命运前途的大事,必定极其慎重,一般须重金延聘风水先生搞定。
崇明是河口冲击岛,乃一马平川的沙洲,自然无山可靠,于是只能在水字上做足文章了;“水汀头”宅院,可谓凝聚着崇明先民智慧的佳作。鸟瞰崇明的“水汀头”宅院,俨然是缩微版的古代城池,古人为御敌,就在城的四周开掘护城壕,无水曰隍,有水曰池。环宅之流水,既是不竭之财源,又能阻隔盗贼,岂不绝妙。江南江北的豪居大宅庭中皆置大缸,或陶土焙或铜铁铸,里面蓄水,以虞毕方造访;岛上“水汀头”宅院虽同为土木之造,庭院中却无需此赘设,此又一妙处。倘若掘河砌屋之时,还有宅院如城池、治家同理国之寓,则虽居处无山峦,胸中有丘壑了,志气恢弘,足以弥无山之缺憾。
日前有幸聆听了北风老师对汉字的解析、对崇明方言的解读,颇长见识,颇多感触;对北风老师集学者风雅、智者风范、长者风度于一身更是满心钦佩。北风老师是崇明方言的专注者,据北风老师考证,究其形,崇明“水汀头”宅院当写作“四桯头”,对此,北风老师一定是花了一番研究功夫的;而我则是随心所思,取其意,更喜欢写成“水汀头”,并擅加揣度以自圆,但期北风老师一笑。
在崇明话里,名词后面常以“头”为后缀,以谐和音节,如言灶为“灶头”、称芦苇为“芦头”、谓路为“路头”,崇明俚语中就有“路头弗熟,苦头吃足”,“水汀头”中的“头”也当作此类词缀解。
而“水汀”也非近代吴地方言中意为暖气的“热水汀”,现代汉语中的“水汀”其实是个舶来词,源于英语中的“steam”一词。如用现代汉语的思维去解读保留着古白话元素的崇明方言,难免会谬以千里的。因此“水汀头”中“水汀”宜分而释之。
《管子·水地》篇称“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水龙经》曰“吉地不可无水”“水积如山脉之住”“水环流则气脉凝聚”。细想来,水是一种“气”,它百转千回经流不息,有自然机变之灵气;它天上地下生生不息,携自新坚韧之锐气。我相信,“水汀头”之水源于此。
“汀”本义是“水平”,后指水边平滩或水中平地,“汀谓水之平也。水平谓之汀,因之洲渚之平谓之汀”。崇明岛坦荡如砥,环水之宅称作“水汀头”宅院应无不妥。
其实“洲”“岛”“渚”“汀”词义相近,只是水势与陆域面积大小不同罢了。位于“洲”中,处于“岛”上,住于“汀”里,这样看来,崇明的“水汀头”宅院建筑思维极富创意,是其他地方鲜能复制的;身居于“汀”,足行于“岛”,神驰于“洲”,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先早就诗意栖居了。
由于历史的变迁,崇明岛上的“水汀头”宅院业已去如黄鹤了;囿于现实的因素,“水汀头”宅院的规模化复兴,也不会指日可待。“水汀头”宅院,是上了年纪的崇明人一个逝去的梦,定格在崇明建筑文化的断层里;崇明方言,这一崇明地域文化不可替代的载体,在年轻的一代崇明人中正日趋式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由此说来,北风老师这样在崇明方言的原野上孜孜不倦的垦拓者,善莫大焉,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