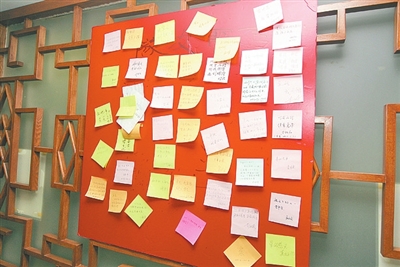茫茫白色中这一抹耀眼的“鲜红”,就是中国目前唯一一艘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号。船体鲜艳的红,船楼圣洁的白。她曾14次赴南极、4次赴北极,出色完成了科学考察与运输补给任务。中国科学家乘坐这条雪中蛟龙,谱写了极地考察的光辉篇章。而雪龙号之所以能屡次于各种极端气候条件下摆脱困境,达成目标,皆因船长沈权过硬的业务素质和沉着冷静的判断应对能力,这样一位“英雄”式人物,是土生土长的崇明人。
今年43岁的沈权出生于崇明县港西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从小就对神秘的大海充满幻想。19岁毕业于宁波海洋学校后,分配到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工作。1994年,雪龙号第一次南极之旅,沈权以三副的身份登上这条船时,已是个“老航海”了。
“向往、兴奋、不安。”回忆起第一次赴南极时激动的心情,这位历经无数考验的船长如今已很淡然,娓娓讲述雪龙号的“传奇”。
雪龙号驶离黄浦江,经过一系列曲折的航线,进入南太平洋。台湾海峡、新加坡、马来半岛、印尼海域的爪哇海,巽他海峡……若隐若现的岛屿、陆上星星点点的灯火,海盗的传说,渐渐消散在深蓝的海洋上。越过赤道后,大海变得光滑如镜。“尤其在夜航时,天空群星闪耀,映照在海面,这样的美景,让我联想到关于大海的种种童话。”沈权说,每当此时,就能感受到最深邃的安宁。
漫长的航海生活终究枯燥。大海上,一浪接着一浪,除了一片蓝,还是一片蓝。这时,科考队员们开始各种紧张的准备工作,搜集资料,彼此讨论各种问题。还有一些队员躲在狭小的房间里奋笔疾书。
“进入南太平洋后,什么情况都可能遇到,风暴、浮冰、冰山……” 历经重重艰难到达南极后,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冰雪茫茫,企鹅从你面前大摇大摆走过,巨大的鲸鱼浮出脊背,喷出高高的水柱,还有数以亿吨计的磷虾,燕鸥在空中盘旋……”这是一个辽阔、绮丽、壮观的白色世界。沈权眼前一亮,内心的澎湃,胜于海面波涛汹涌。
2005年11月18日,是沈权担任船长以来的第一次南极之旅,他首先要接受的严峻考验,就是让雪龙号安然穿越“喜怒无常”的西风带。
“魔鬼西风带”,多少航海家谈之色变。位于南纬40°-80°之间的这一区域,不断生成的气旋酿成风暴,雪崩般的巨浪连绵袭来,即使是有着现代化设施的巨轮,也不得不忌惮几分。许多船只来到这里之后,面对巨浪和风暴不得不调头返航。
然而,沈权明白,肩负祖国科考重任、身系人民重托的雪龙号,唯有破冰斩浪,勇往直前。“我相信,凭着丰富的经验和全体船员的同心协力,一定能突破‘魔鬼’的封锁。”
一路向南。
在澳大利亚弗林曼特港短暂停留后,雪龙号继续前进。离西风带越来越近了。沈权不停查阅各种气象资料,分析数据,他大胆采用美国有较强针对性的气象预报系统发布的短中期预报资料,以便及时调整速度、航向,选择恰当时机绕过气旋,或找到缝隙穿越。
终与“魔鬼”相遇。狂风席卷着巨浪蜂拥而至,扑向船舷,浪涛在剧烈的撞击中化为一片迷梦般的水雾,然后渐渐消散,接着,又一片水雾腾空跃起……雪龙号一会儿被抛到浪巅,一会儿又跌至波谷,这艘钢铁巨轮在茫茫大海面前显得如此渺小、命运难测。
这时,沈权通过分析多种资料作出准确判断,一边调整航向,一边果断绕行,雪龙号不时与大自然的锋芒擦肩而过。沈权同时指挥船员们不停地对船上的物资进行加固定位,决不允许一根钢缆松动,船只在风浪中艰难地保持着平衡。4昼夜后,雪龙号安全驶离西风带。
极地生存环境恶劣,漫长的极昼夜如影随形。在极昼中睡觉,醒来后不知是“白天”还是“夜晚”,让人觉得一切没有尽头。然而,奇迹往往是在突破“极限”后被创造的。
沈权清晰记得第四次赴北极科考的惊心动魄。“当时希望能到北极点。但在冰区里航行非常耗油,冰层厚度如果超过雪龙号的破冰能力,后果无法估量。”我国第三次北极作业的最北点是北纬85°25′,每往北1′,雪龙号都在挑战极限。
回头抑或继续前行?一切都是未知,又是那么吸引人。
“闯!先让飞机侦察找到水道,然后在电子航图上标出来,照此航行。”凭着对雪龙号性能的了若指掌和不断的分析考量,沈权毅然做出了决定、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鲜红的雪龙号昂首驶入一片白茫茫。
北纬88°26′,第四次北极考察,雪龙号创造了中国航海史上迄今为止的最北点,沈权也成为中国第一个登上北极点的科考船船长。来不及释放兴奋和好奇,科考队员已经开始观测采样,为我国研究神秘的北极点收集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有惊无险的故事不少。中国第27次南极考察,雪龙号在指定地点停泊后,开始卸货。首先是CAT车,所有的物资,都靠它输送。“咔!”当这辆重达25吨的庞然大物驶上冰面时,所有人都听到了冰裂声。
劲风如刀,心头狂跳。
“铺木板!”沈权和大家一起,6人扛一块木板,在冰面上为车子铺路,一点点推进。如履薄冰、步步惊心。终于,“大家伙”顺利到达目的地,物资输送畅通无阻。
每年11月出发,次年回国,雪龙号每次出航,至少5个月。漫漫征程,何以解忧?
“船上设有游泳池、图书馆、篮球场、卡拉OK可以消遣。” 沈权说,船上生活不算太单调。到了南极,完成任务休整时,大家还会在冰面上踢足球,插上两根旗杆作球门,热闹的气氛吸引了很多企鹅前来观赏,它们和雪龙号上的船员、科考队员们同样感到好奇,企鹅们不知道自己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发生了什么,却成了足球赛最忠实的观众。
随着极地科考次数增加,兴奋和好奇渐渐淡去,残酷的环境、神经时刻紧绷的作业成为主旋律。“从做大副开始就没有休过年假,十年了,春节都是在船上过。” 沈权清楚记得,首次去南极考察那年,恰逢女儿出生。记不得是哪一年回家,当他满面春风地出现在女儿面前时,可爱的女儿礼貌地朝他鞠了一躬:“叔叔好!”沈权顿时五味杂陈。
今年女儿高考后,沈权陪她去了云南,作为补偿。和所有雪龙号船员一样,沈权深埋着对家的愧疚,却无愧于科考事业,无愧于一个大写的“人”。
极地科考冷酷而残酷,是什么让沈权和雪龙号始终坚持前行,屹立不倒?是成功后的巨大喜悦,是不忍割舍的感情,还是挑战极限的刺激?
今年8月,雪龙号在崇明整修,沈权又回到了熟悉的土地。10月底他随船离港,再赴南极。也许,雪龙号的再次起航,能回答所有这些问题。
地球两极,一条雪中蛟龙乘风破浪遨游大海,五星红旗在船头猎猎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