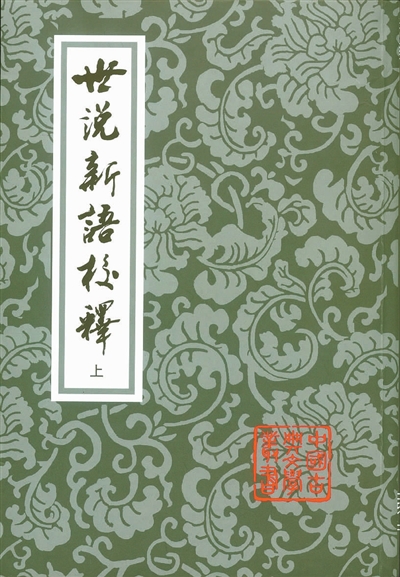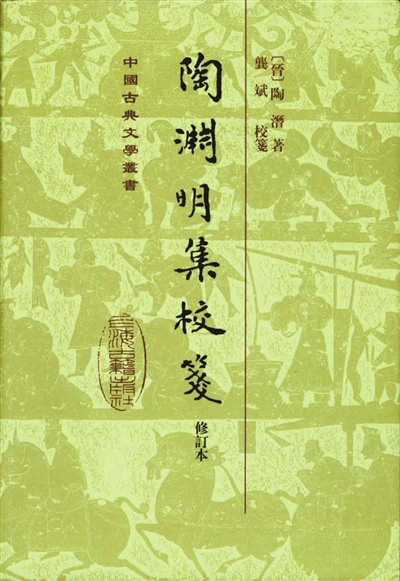老去了十年光阴,我写完了《世说新语校释》。伴随我虽有春花秋月、夕岚晨曦,但更难忘酷暑、严寒,尤其是孤独与寂寞。
开始是畏难,后来是彷徨,最终选择不放弃。从此心不旁骛,奋然前行。
《陶集》我最爱,《世说》亦屡读。在中古文学的华苑里,《陶渊明集》和《世说新语》是我最爱读的二部文学名著。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拙著《陶渊明集校笺》问世之后,阅读和研究的兴趣转向《世说》。新世纪伊始,我给硕士研究生讲过几年《世说》研究的选修课。授课之余,写了几十篇读书札记,考辨、解读此书中一些意蕴特别丰富的条目,并发表过一部分。
在阅读和研究《世说》之初,我就把陈寅恪先生作为最值得效法的榜样。寅恪先生《世说新语文学类“锺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支愍度学说考》等研究《世说》的论文,探幽索隐,胜义迭出,使我敬佩不已。再有,据说寅恪先生曾有过注释《世说》的计划,后来因为战乱致数据散失而未果。这件事常引起我的想象:寅恪先生未能完成的《世说》注释,该是什么样子呢?我猜想,很可能与他上面几篇论文相去不远,必定是抉发《世说》的历史文化底蕴。受寅恪先生论文的启示,遂萌生注释《世说》的念头。
可是,这一念头存想有年,却不敢贸然付之行动。主要原因是自思功力不够。寅恪先生的论文高标云汉,可望不可及。即或是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也是博大精深。余氏耗时十几年笺疏《世说》,自称“生平著书甚多,唯此书最为劳瘁”(见该书前言)。我与前辈相比,识见不卓,读书不博,欲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谈何容易?又以为解读《世说》工作量大,而来日苦短,完工真不知在何年何月。于是犹豫徘徊,畏修途而作罢。
但钟爱的东西,会常常浮现心头。彷徨之余,我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我认定,年在桑榆,仍然有可能出现灿烂的晚霞。人生的唯一价值,难道不就在精神的创造么?权力、金钱、名位,无不被雨打风吹去,唯有精神可以绵延至永远。终于,我从畏难、犹豫中走出来。解读《世说》的念头遂越来越强烈,以至焦躁不安,似乎灵魂都在燃烧。我觉得应该赶快做,完成我的夙愿。即使最终或许书稿篇幅过大之故,无出版的机会,那么,把手稿送给图书馆,也能给后来者参考。为什么一定要预先保证事情的结果呢?应该先尽力于它的过程。再说,没有过程,何来结果?这样一想,心态渐趋平静,畏首畏尾变为勇敢前行。
从二OO五年下半年开始,由撰写读书札记转到集中力量校释《世说》。每天上午、下午、晚上,像开足马力的推土机,札札实实地向前推进。不停地写,反复地改。经过整整五年的劳瘁,到了二O一O年春天,终于完成了全稿。加上之前写作札记的时间,算来前后已有十年了。
有关《世说》的校注本,目前流行较广、价值较高的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杨勇《世说新语校笺》、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其它以普及为目的的注释本更多。这些著作,对于普及《世说》和推动《世说》的研究,都作出过或大或小的贡献。但学术总须新变,总要反映每一时代的文化和审美意识。我理解的学术史是环环相扣的链条,每一环都自具特色。我们接续前辈,在接受他们的赐予之后,又须作出新贡献,赐予后来者。每一时代的学术既是继承,又是创新;既是传统,又是现代。本着这样的认识,我在校释《世说》时,尽量吸收最近几十年来新的研究成果,注重实证和考辨,提出自己的见解。
除了吸取国内学者的成果之外,还参考十七、十八世纪的《世说新语》的日本注本。我发现一二百年之前的日本学者对《世说》的研究已有相当深度,常有真知灼见。根据国内几家图书馆联合编写的目录,在上海找到了四种。二OO九年十一月,沈阳已是寒风刺骨。我到辽宁省图书馆查找日人竺常的《世说抄撮》十卷。馆里的工作人员倒是热情地接待我,在馆藏目录查到有此书,然而很奇怪,却找不到卡片,末了遗憾地说:“不知道书放在什么地方。”使我千里寻书,抱恨而归。又过了一个月,我请南京大学的校友帮忙,查找南京图书馆所藏日人田口颐的《世说讲义》。目录上有这部书,但图书馆告知该书已封存,读者不能借阅。为何封存?为何不让借阅?何时能够借阅?一切都没有解释。真是咄咄怪事!叹息之外,我又能何为?现在,拙著仅参考了四种日本旧注本,敬请读者谅解。
回顾自己读书和研究的经历,基本上为兴趣所左右。我喜欢中古文学的奇情异彩,尤钟情于魏晋。故读三曹诗、读陶渊明、读《世说》、读谢灵运,津津有味,不觉怠倦。沉潜赏玩久了,若有所得,便发而为文。往昔校笺《陶集》,中间研究青楼与中国文学之关系,后来校释《世说》,颇似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乘兴而行,兴尽而返。有兴趣含英咀华,无兴趣味同嚼蜡。读书、研究好比恋爱,苟非所好,勉强为之,结果唯有痛苦而已。只有感觉兴趣的书,有趣味的问题,才有可能长久地钟爱她,迷恋她,终生为之缠绵,而决不放弃。《陶集》和《世说》,便是我的最爱。二十多年来,我沉浸在这二部名著中,忻忻然不知老之将至。
当然,在现行的学术研究管理体制下,凭兴趣的研究,往往得不到项目经费的资助。我先后校释《陶集》、《世说》,没有得到过分文资助。但此有何妨!没有经费资助,照样能作出有水平的研究。学术的本质是精神创造。精神创造虽亦“有待”——须物质的支撑,但终究与金钱无必然的联系。唯有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独立,才是文学艺术创造的首要条件。揣摩上面的意图,钻研弄钱的诀巧,请托奔走,四处折腰,志如此屈,情何以堪?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我凭兴趣研究,不靠立项资助,不存在“欠债”的心理负担,所以能比较从容地赏玩所喜爱的作品。庆幸我三年前从讲台上退下来后,无开会之干扰、填表之无聊、评估之作假,获得了自由创造的更大的空间和充裕的时间。这部书的撰写,使我再次深切地体会到,没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以项目经费的有无多少作为衡量学术的主要标准,不仅滑天下之大稽,而且会严重毒化学术环境,会绑架学术,彻底扼杀学术。
熊十力说:“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致徐复观书》)十力老人的警句,指出了知识和人格双重堕落的原因,这在浮躁虚假之风弥漫天下的今天,尤具警世意味。潜修和枯淡,必然自放于寂寞之境,与孤独为伴,无缘鲜花和掌声。然而,远离浮名和虚荣,得到的却是自由和宁静。只有孤独、寂寞,才能内视自身,遐观六合,烛幽照冥。惟有静境,才适宜精神的创造。试看历来的人格修炼者、文学艺术的探索者,有几人不是孤独和寂寞?先哲云:“守寂寞而存神。”(《后汉书·冯衍传》)只有身处寂寞,才能用志不分,拒绝外部世界的诱惑,神清而气爽,淡泊而充实。寂寞孤独,实在是精神创造者的乐地。追求精神和艺术的高标者,也必然会踵武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枯槁而不改其度,憔悴也自得其乐。自然,十力老人的话,只可说与追求知识和品节者听,而未可为慕浮名、爱虚荣者道也。可叹黄钟大吕,将至沉寂,遑遑然奔走之徒,几人能谛听希声之大音?
二十多年来,我结庐人境,轩冕有时而过,故偶尔也“未能免俗”。但我的大部分时日,远离高谈阔论、觥酬交作之地,而宁愿选择孤独和寂寞。我默默地磨砺我的剑。先是用了八年的时间,撰写《陶渊明集校笺》。于我而言,沉潜《陶集》的八年,是求知求真的探索经历,也是祛浮名、弃虚荣的人格修炼的过程。尔后,我又写出了《陶渊明传论》。彷徨数年后,再用十年时间,完成《世说新语校释》。在漫长的岁月里,我出入于陶渊明和魏晋名士之间,尚友千载,真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味道。当年,谢安称谢鲲道:“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我读《世说》于此,常会心而笑。惟恨碧落黄泉,罕遇七贤。然“越名教而任自然”,摆脱拘束,保我本真,放飞心灵,于孤独寂寞中庶几可至。我爱陶公真率,亦慕江左风流,但以我性情而言,终究觉得陶公亲近。那位一生枯槁,咏唱“万族皆有托,孤云独无依”的高士,才是我服膺的精神导师。因此之故,我也终究学不来做学林“名士”,而止宜为学林隐士也。
虽说十年一剑,但我自知此剑远非锋利如切玉之刀。材料有待充实,语言尚未雅洁,见解未臻精妙。《世说》作为魏晋时期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名著,如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我尝试解读之,虽然稍有所得,但离揭示她的深厚内涵尚远,有些地方仍一知半解。我希望喜爱她的读者和研究者,在指出拙著的谬误与不足的同时,能集思广益,一起来解读《世说》的奥妙。
最后,我要再次表达我的感恩之情。首先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先生。没有昌平先生的知遇和帮助,拙著不可能问世。他一开始就要求我一定要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我始终记住他的鞭策,坚持精品意识。再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的《陶集校笺》的出版,也与昌平先生的关爱密不可分。现在,当我左《世说》、右《陶集》之时,满怀对昌平先生的感激之情是非常自然的。
在拙著撰写过程中,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为我查找域外图书数据提供了方便。我的同事沈茶英老师,学生金柯、魏明扬,前几年跟我一起学习的日本留学生大立智砂子博士,也为我查找资料出了不少力,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斗转星移。院子里的那棵老葡萄树不知经过多少回的衰而荣、荣而衰,主干上的皮裂开成条状,褐色,薄薄的,像寒风中的褴褛衣衫。时已深秋,枝上是枯叶,树下还是枯叶。看到它,不由想起《世说·黜免》中殷仲文的感叹:“槐树婆娑,无复生意。”其实,等到春天,老树也可再荣。至于人生呢,却注定要被日月无情地掷向衰损之淖中,直至灭顶。我真不知道上帝能否再赐予我足够多的孤独和寂寞,让我能以日渐衰损之力,将余生的全部,投之于烈焰,化成一支新的、锋利的剑。